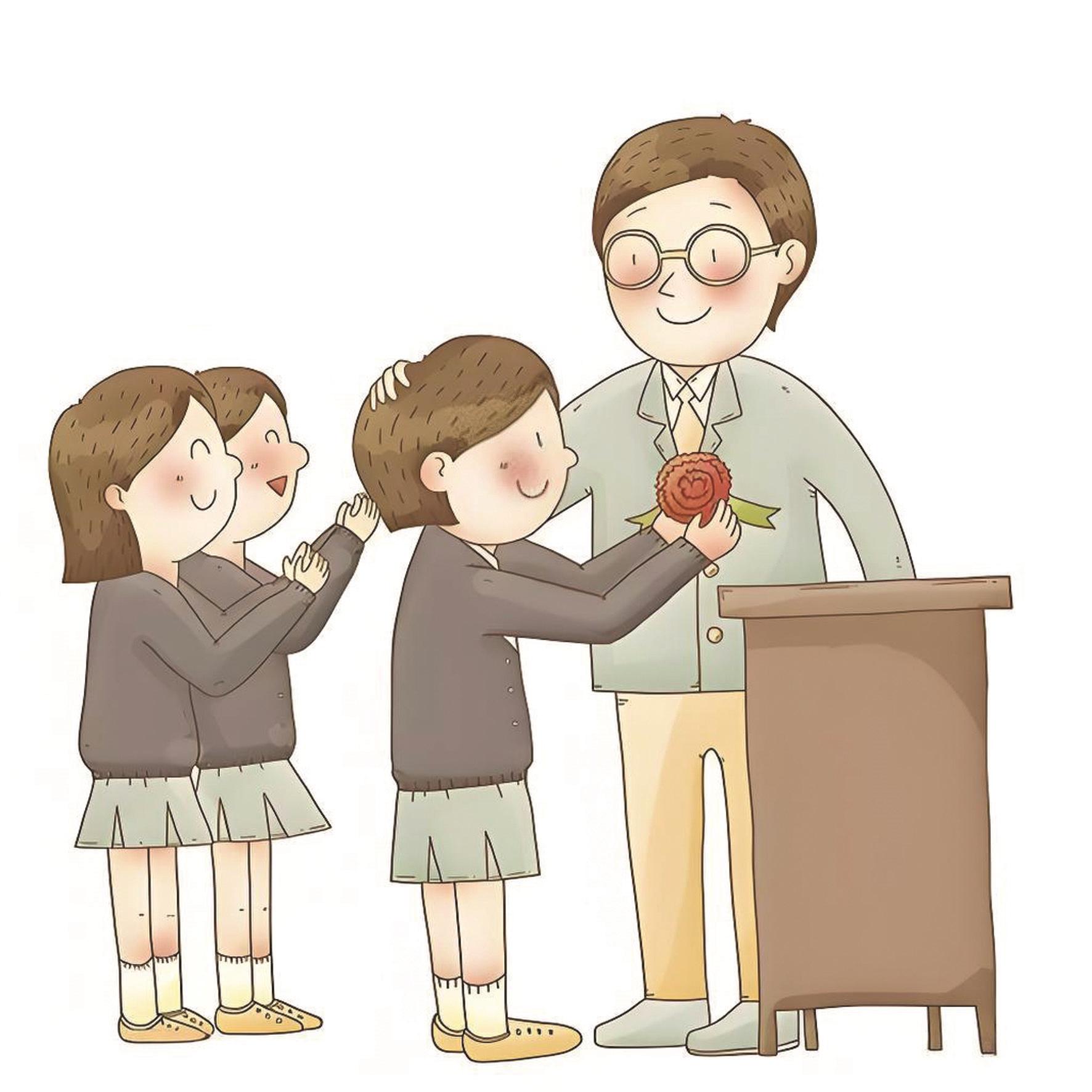□张秉毅
悠悠四十载,弹指一挥间。1985年,我带着几分懵懂和青涩走上了讲台,那一年有了第一个教师节;2025年,再过很短的时间,我就要告别讲坛,结束自己的教学生涯。回过头来看,近乎半个世纪,很长,但也很短,一切都在昨天,一切也都似乎刚刚开始,甚至时不时地感慨:似乎尚未登台,竟已悄然落幕。
常常试图回头寻找40年的足迹,但实在乏善可陈。惆怅多于喜悦,失落大于欣慰。再前几日,把两个办公室整理一下,把自己的东西带走,除了书,还是书,几乎没有第二样的东西,装进纸板箱,搬进车子后备箱;把电脑里的材料或下载或清除,然后独自一人坐着,看着空荡荡的办公室,看着电脑翻动的屏保,内心惆怅又忧伤。
即将挥一挥衣袖,告别这个工作了二十几年的地方,这个熟悉的校园,我会留下些什么呢?校友捐赠的景观石、拓荒牛,以及学生宿舍区的匠心亭,铜质铭牌上所有的文字均出自我手,也许今天还有几个人知道它们的作者是谁,但我敢肯定,要不了多久,谁也不再知道这个人,那里连一个落款都没有。
对岁月不居、人生苦短的感慨,这是人类永远的命题。人总得顺应规律,顺应规律是一种哲学的表达,但理性是一回事,感性又是一回事。人有感性,才会有忧伤或快乐的情绪,才会有种种的自诩与遗憾,以及种种感慨,但正是有了感性,生命才有滋味,才真实。果真太上忘情,那人生多么无趣。不过我还是喜欢高僧的一句话:“一切都会过去”。
孔老师有弟子三千,我虚荣地 想,我弟子的数量应该超过三千吧,一级一级迎来,一届一届送走,在一次又一次的目送中,也目送了自己的岁月,从青年到壮年再到暮年,目送着自己的余生慢慢变短,过去的光阴慢慢变得悠长。无数个日子似乎是一天一天地复制粘贴,但日子就是这样在叠加中减损,如水如风般地逝去了。
我不大愿意参加学生的毕业照相,除了早年带班主任的时候,再后来做一个普通的任课老师,就不再参加了。主要原因是自己好静,好独处,喜欢孑立在人群的边缘。还有个原因是,我不知道是让他们记住我好呢,还是忘掉我更有利于他们去快乐地生活,更何况,记住,也并不在于照片上有我那煞风景的容颜。
以前,每一届我给他们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,总会喜欢向他们说几句祝福的话,希望他们高考顺利,同时,总会重复这样的一句:你们记住我,会知道该怎样去生活;而忘了我,你们才能活得更好。而今年,我上完最后一节课,向他们告别并献上祝福,我说,这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一节课,也可能是我今生所上的最后一节课了。这样说完的时候,忽然哽咽了,差一点落泪,全班响起热烈的掌声,我不知道那掌声是一种怎样的含义,在掌声中我不敢再看他们,我害怕当着他们的面泪水倾泻下来,我赶紧转过身,挥挥手,快步走出教室。
在教室里哽咽,这是第二次。第一次是早年给学生上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,给他们读课文,读到“天气愈冷了,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?我们是有的。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?”便无法控制地哽咽,不能继续读下去,后来再上这篇课文干脆不再范读。
我留给学生的背影是怎样的呢?迂腐的,瘦弱的,坚强的,忧伤的,遗憾的,慈悲的——我无法确定。我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,所以我常常操之过急,情绪一失控,便会有粗暴的态度和尖锐言辞,尽管用心是好的,但方法的失当,言语的犀利,难免会伤了师生的情感,伤了孩子的自尊,也有辱斯文。
虽然我对他们的批评从来都是因为学习,或者遵守纪律上出了问题,从来没有因为私事,我也从不让孩子们为我做任何私事,尽管曾有一个孩子会趁我不在的时候把我办公桌整理得整整齐齐,我的批评,我的怒火,多多少少带有一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,因为我把他们当作我的孩子,我那么焦急的迫切的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轻松的有尊严的人生。尽管可以用“爱之深,责之也苛”来为自己解脱,但终究难以释怀。
“有时不能忍,猝然发雷霆;继思不太妥,道歉亲上门”,这是陈毅的话。我常常这样,每每大光其火之后,被我批评过的孩子说不定早已安然入梦,但我则辗转反侧,悔恨着自己又犯了一次错误,次日上课一定会首先对昨日之事鞠躬致歉。这种事情在我的身上不止一次地发生过,这是我最大的毛病,也是我最大的遗憾。
我的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们,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把我当成老师,是否认可我这个老师,因为我知道,不是所有站在讲台上的人,学生都会把他尊之为师的。有的人当了一辈子老师却没有一个学生。我很怕我也是这样的人,所以我特别期待你们能够公平地评价一句:这个老师是负责任的,这个老师是有良知的,这个老师没有误人子弟。这于我而言是最高级的勋章和最华美的桂冠。
提前告个别,向我付出了一生心血的讲台。没有资格说再见。
我将去哪?在云起时,在水穷处。
(作者单位:天长工业学校)